集权是一种必然
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,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,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、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。实际上,对于如何支配资源、分配财富,人类进行了各种尝试,探索了许多方案。比方说,根据武力的强弱、资金的多少,或者权力的大小,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。这就形成了三种社会类型,即武力社会、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。部落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,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,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。邦国的特点,是半武力半权力,并由武力过渡和转化为权力,或者说借助武力获得权力。因此,邦国必将发展为帝国。帝国,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。它的特点,就是集权。
这是一种必然。
众所周知,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,而“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”,按照恩格斯的说法,又“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”(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)。在资源稀缺、财富不多、族群较小的情况下,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主要靠自然法则来分配。比如在摩尔根和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时代,也包括野蛮时代前期,猎物和谷类基本上由族群的成员共享。但如果入不敷出生存困难,则年老体弱者就将被淘汰出局。他们将被分配到较少的食物,被杀死或令其自杀,甚至被吃掉。因此,即便在这种自然法则中,我们仍可以感到某种力量的存在,比如风俗的力量,习惯的力量,自然的力量。
毫无疑问,这三种力量,只可能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前期发挥主导作用。到野蛮时代后期,人类已经掌握了制陶、养植和金属加工的技术,社会财富空前增长,社会需求也空前增加。这时,风俗的、习惯的、自然的力量已不足左右社会,也就必须让位于另一种力量,即“武装的力量”。事实上,野蛮时代部落之间的战争是没有休止的,能够成为一名战士也极其光荣。那时,一个人,如果战功显赫,他就会得到部落的奖赏和女人的欢心;而一个部落如果足够强大,它就会吞并其他部落。这种吞并开始是在小范围内局部地发生,即就近吞并。这就是柳宗元所说的“近者聚而为群”(《封建论》)。吞并的结果,是小部落变成了大部落。大部落之间也要互相吞并。如果吞并不了,或者要共同对付更大的部落,它们就会组成部落联盟,以武力最强大的部落为领袖,这就是“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”(各部落首领听命于最强大部落的首领)。
在这里,“听命”二字至关重要。它说明什么呢?说明部落联盟的领袖已经主要靠行使权力来管理社会了,尽管这权力是依靠武力来获得、来支持的。但不管怎么说,武力已经开始向权力转化,这就为过渡到权力社会奠定了基础。也就是说,战争的结果,一方面是资源和财富逐渐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个人或集团手中;另一方面,这个或这些特别有武力的个人或集团,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。因此,当某一集团(比如秦国)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,武力社会就必然会过渡到权力社会,由初级形态的国家(邦国)变为成熟形态的国家(帝国)。正因为如此,权力社会的统治集团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。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,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,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。
只有希腊是一个例外。希腊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,也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,从野蛮到文明,从武力社会到非武力社会的演变过程。不同的是,希腊人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变成权力社会,而是变成了财力社会。这些北方来的高大白皙的雅利安人原本是蛮族。当他们移民到希腊半岛时,就像范缜所说的落花,有的落在了枕席上,有的落在了茅厕里。那些落脚之处土地肥沃的,就一直务农下去,并建立起“半权力社会”。这就是斯巴达。土壤贫瘠的,则改事航海、殖民和经商,并建立起“半财力社会”。这就是雅典。财力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,遵循的是市场规律,讲究“契约面前人人平等”,并由此产生出既保护又约束全体公民的“全民公约”或“社会契约”──法律。在法律面前,就像在契约面前一样,是人人平等的。因为人人平等,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、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。也因此,财力社会与专制或集权不相容。还因为此,民主与共和只能产生于财力社会,即只能产生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。其他国家(武力社会或权力社会)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与共和制度,只能从商业国家输入,或向商业国家学习。
诚然,民主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。雅典城邦公民投票处死苏格拉底,就是民主制度史上的耻辱和污点。但这些缺憾是可以修正的,民主也至少是迄今为止“最不坏”的制度。同样,财力社会也不一定就比武力社会和权力社会美好。武力社会的英雄气概和权力社会的温文尔雅,在财力社会很可能会被代之以恩格斯所谓“庸俗的贪欲、粗暴的情欲、卑下的物欲”,代之以寡廉鲜耻的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。资本控制的社会甚至有可能走向专制。如果资本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或某个集团手中,就会造成垄断,正如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或某个集团手中就会造成独裁一样。垄断和独裁,是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。
这就需要警惕,而财力社会(即市场经济社会)的态度是旗帜鲜明地反垄断、反独裁。因为垄断也好,独裁也好,都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本性格格不入。对于商业社会来说,没有什么比经济自由更重要。经济的自由,正是其生命的活力之源。然而市场一旦被垄断,竞争就不再自由;而竞争不再自由,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。因此,资本主义各国一定要制定诸如《反垄断法》之类的法律,来确保自己的生命活力不被窒息。
非市场经济社会的情况则又不同。
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也有两种,即权力社会和武力社会。游牧民族是比较钟情于武力的。靠着武力,他们往往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,所向披靡。但马上得天下,并不能马上治天下。如果像成吉思汗那样“只识弯弓射大雕”,建立了政权,也不可能长治久安。这就要向精于此道者学习。学得好的,就呆下去(比如清);学得差的,就呆不长(比如元)。
擅长建立稳固政权的只能是农业民族。农业生产需要精耕细作,需要耐心等待,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过多地使用武力显然于农耕不利。春秋战国时代,甚至有秋季才能出兵的规矩(帝国时代则演变为秋季处决人犯的惯例)。这正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限制使用武力(秋后粮饷较足也是原因之一)。因此,农业民族更热衷的是权力而非武力。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造成对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的破坏,但其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。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在别无选择的前提下,农业民族宁要暴君,不要暴民;宁肯臣服于皇帝,也不愿依附于流寇。只有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,才会揭竿而起。但在这时,他们是把起义领袖视为“真命天子”的,而且希望这些领袖一旦打下了江山,就立即放下屠刀,拿起权杖。也就是说,农业民族的选择,是建立权力社会。
然而不幸的是,权力社会原本来自武力社会,权力集团也必定产生于武力集团。即便是那些依靠“和平手段”夺得江山者,比如曹氏父子(魏)、司马家族(晋)、赵匡胤兄弟(宋),哪一个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坚强后盾,又哪一个不是军阀?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,即权力社会很容易变成集权社会。因为对于战争的胜利而言,集权是必须的。如果一个部落或民族长期使用武力,那它就必定集权,甚至会产生专制和独裁。当然,集权未必专制,专制也未必独裁。比如唐代制度规定,皇帝的旨意,必须得到宰相议事机构──政事堂会议的认可方能生效,就不独裁。但不管怎么说,集权则是必须的。
好在这并不成问题,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。正如马克思在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一书中所说,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“一袋马铃薯”。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,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。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,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,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,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,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。”因此,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,只能由我们这样的农业民族发明出来。或者说,当农业民族进入到文明时代时,他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权力社会,甚至集权社会。
从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,这是一个进步,因为社会运作的成本明显降低了。过去,为了支配资源,分配财富,必须付出血的代价,正所谓“争地以战,杀人盈野;争城以战,杀人盈城”(《孟子·离娄上》)。这对于整个人类而言,无疑巨大的灾难。现在,“硬打拼”变成了“软着陆”。只要一声号令,一道文书,便可令行禁止,岂不是节约?节约下来的人力物力可以用来发展生产、改善生活,人民群众也可以安居乐业,岂非进步?
所以,帝国制度建立之初,不但统治阶级意气风发,以为是替天行道,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额手称庆,欢欣鼓舞。按照贾谊《过秦论》的说法,秦始皇“并海内,兼诸侯,南面称帝,以养四海”,建立起自己中央集权的王朝时,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抗。相反,那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(天下之士斐然向风),并对它抱有极大希望(莫不虚心而仰上)。这应该说是一个事实,因为民众总算不会动不动就被砍掉脑袋了。“元元之民”既然能“安其性命”,自然感恩戴德,山呼万岁。实际上,大秦帝国过早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这里──他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。权力是一种“非典型暴力”,然而始皇和二世却把它当作典型暴力(武力)来使用,岂有不亡之理?
秦虽二世而亡,汉却继承了秦的事业并获得成功。这说明集权和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要求,秦与汉则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。事实上,仅是水灾和饥馑,就要逼出一个中央集权来。那时割据的诸侯,除秦国以外,几乎无不以邻为壑,比如修筑不利于他国的堤坝,在灾年禁止谷米的流通。公元前332年,赵国与齐魏作战时,竟然将黄河决堤以浸淹对方,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贫苦无告的民众。天灾加上人祸,如再不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集天下之权,那可真是民不聊生!事实上,秦始皇就宣称自己的功劳是“隳坏城郭”和“夷去险阻”,即国内不再设防,粮食全部流通。可见集权一事,在当时还真是一个福音。
更何况,那时也没有别的路好走。封建制度(邦国制度)已弊端尽显,民主制度(城邦制度)又闻所未闻,除了走向集权,又能如何呢?
现在需要的,只是为它找到一种形式,并使之制度化。
于是,帝国被发明了出来。
王朝的气数
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,到公元1911年清朝廷交出政权,二千一百年间,中华大地上建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。这些王朝,大体上都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。那么,它们的命运如何呢?或者说,帝国的历史如何呢?
让我们做一个回顾。
如果以所谓“五代十国”为界,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。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,到公元907年朱全忠(又叫朱温、朱晃)灭唐,共1128年,是为上半段。从这一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,共1004年,是为下半段。上下两段的年头,只差一百二十多年,大体上还是对称的,堪称“上下两千年”。
上下两段的结构也很对称。上半段有四个统一的王朝,即秦、汉、隋、唐。下半段也有四个统一的王朝,即宋、元、明、清。上半段的秦汉与隋唐之间,夹了个半统一的魏晋南北朝;上下两段之间,则夹了个半统一的五代十国。五代十国在帝国史上是个异类──中原五个汉胡杂鞣的小朝廷,周边十个不成体统的小帝国(实为王国),就像五道热菜加十个冷盘。中原那五个小朝廷,走马灯似的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,而且国号都有个“后”字: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。之所以叫“后”,是因为此前已经有过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了。可见这些立国的武夫,是一点创造性都没有的。周边十个小王国,吴(扬州)、南唐(金陵)、前蜀(成都)、后蜀(成都)、吴越(杭州)、楚(长沙)、闽(福州)、南汉(广州)、南平(江陵)、北汉(太原),就更是七零八落可怜兮兮,而且前前后后此起彼伏,简直就是一场闹剧。这些小朝廷的寿命也很短:后梁17年,后唐14年,后晋12年,后汉5年,后周10年,十分短命。十国的历史长一点:吴46年,南唐39年,前蜀35年,后蜀40年,吴越86年,楚56年,闽53年,南汉67年,南平57年,北汉29年。但这些小国不过割据一方,苟延残喘,并不能算数。而且,按照“正统”的计算方法,整个五代十国总共只有53年,因此我们宁肯把它看作帝国史上的一个小插曲。
由这个小插曲分隔开来的帝国历史上下段也十分有趣。上半段四个王朝,隋唐是秦汉的翻版;下半段四个王朝,明清是宋元的翻版;而下半段中的宋,又可以看作是上半段中晋的翻版。晋和宋,都是后来只剩下半壁江山,只不过一个是东西(西晋东晋),一个是南北(北宋南宋)。甚至就连他们夺取政权的方式都一模一样。晋武帝司马炎是向十五岁的少年皇帝曹奂(魏元帝)逼宫,宋太祖赵匡胤则是向七岁的娃娃皇帝柴宗训(周恭帝)夺权。他们都是“篡”,都是“谋逆”,都是宫廷政变,都是欺负孤儿寡母,或者说,都是使用“非武力手段”。不过,司马炎虽然轻而易举地夺了人家的江山,却没安排好自家的事务,结果晋成了一个既短命又分裂的王朝。中国历史上有短命的王朝(秦15年,隋37年),也有分裂的王朝(宋)。但秦和隋虽然短命却不分裂,宋虽然分裂却不短命(319年,仅次于汉),短命又分裂就只有晋。晋虽然说起来也有155年,但正儿八经算是个统一王朝的,也就是从公元280年武帝灭吴,到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这10年,以后就是自相残杀、抱残守缺和坐以待毙,黄仁宇先生便认为它“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”(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),我们也主张把它看作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期的组成部分。
其余八个统一的王朝,又可分为四个阶段。秦汉为第一阶段,隋唐为第二阶段,宋元为第三阶段,明清为第四阶段。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是同一种模式,即前面一个较长时间的动乱状态(春秋战国501年,魏晋南北朝369年),后面一个虽然短促却具有开创意义的王朝(秦15年,隋37年),然后是一个强大的、兴盛的王朝(汉426年,唐289年)。而且,这两个强大兴盛的王朝又都曾断裂过一次。汉当中插入了一个不怎么算数的王朝,即王莽的“新”,并被明确地分为西汉和东汉。唐则插入了一个更不算数的王朝,即武则天的“周”。不过,唐虽然没有被分成什么“西唐”、“东唐”,或者“北唐”、“南唐”(历史上那个“南唐”是另一回事),但许多学者都认为,以“安史之乱”为界,初唐、盛唐,与中唐、晚唐,实为两截。如此,则帝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,就完全是一个模式了。
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同为另一种模式,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,后面一个少数民族王朝。赵宋(319年)的后面是孛儿只斤氏的元(97年),朱明(276年)的后面是爱新觉罗氏的清(267年)。汉、唐、宋、明,这四大帝国,前两个主要亡于内乱,后两个主要亡于外侵。当然,汉唐末年,外族也趁火打劫;宋明末年,内乱也烽烟四起。结果,北方的两个少数民族武装乘虚而入,颠覆了汉族政权。
帝国的历史,大抵如此。
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、完善的过程。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。秦创郡县制,汉因之;隋创科举制,唐因之;宋创文官制(文臣将兵制),明因之;明创阁臣制,清因之。然而越是集权,就越是糟糕。帝国历史的后半段,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。宋是丧权辱国,元是天怒人怨,明是萎靡不振,清是死气沉沉。所谓“康雍乾盛世”,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,论气度,论胸襟,论精神,均不能与“汉唐气象”相提并论。因此这又是一个由强到弱、由盛到衰的过程。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为标志,是“积强”。强到不能再强,崩溃。以澶渊之盟和辛丑条约为标志,是“积弱”。弱到不能再弱,瓦解(请参看本书第五章)。前面四个王朝(秦、汉、隋、唐),是自己把自己打死;后面四个王朝(宋、元、明、清),是自己把自己闷死。总之,帝国制度越是完善,越是成熟,越是精细齐备,就越是走向死亡。
实际上帝国早就该死了。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以后,它就事实上不再有创造力和生命力。后来那些“发明创造”,都不过雕虫小技。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“大唐盛世”,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369年的魏晋南北朝。
魏晋南北朝是帝国史上一次极大的反常。经济基础、上层建筑、意识形态,都发生巨大变化。首先是东汉帝国的大厦在宫廷政变和军阀混战中轰然倒塌,然后是一系列的王朝更替和外族入侵,刀光剑影天翻地覆,城头变幻大王旗。在北方,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,五胡乱华。少数民族枭雄相继问鼎中原,不断建立起五花八门历时极短、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色彩的新政权。中原地区汉胡杂处,比例倒挂。少数民族逐渐汉化,汉民族同时也在不断“胡化”。在南方,庄园坞堡林立,豪雄拥兵自强,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,纷纷投靠豪门,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以外的“部曲”和“荫户”,地主经济退化为领主经济。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安。朝代迭次更替,政局极不稳定,唯一的统一王朝西晋,竟然重新实行“封建制”。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公、郡公、郡侯、县王,而且有职有权,可以管理境内的民政、财政和军政,封国多达二十一个。前有三国鼎立,后有六朝更迭,整个魏晋南北朝,变成了春秋战国的汉胡杂鞣版。
然而,这个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分裂、局势最混乱、社会最痛苦的时代,却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。唯我独尊的儒学摇摇欲坠,异端邪说反倒风靡一时。六经注我取代了寻章摘句,标新立异压倒了因循守旧,离经叛道成为学界时尚。在统治阶级无法进行强有力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,“家弃章句,人重异术”(《宋书·臧焘传》),论辩成风,“是非蜂起”(刘伶《酒德颂》)。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前导,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,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席卷全国,魏晋南北朝成了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的丰收期。
这就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。事实上唐帝国的成功,原因之一就是以“儒道释并存”的“三教合流”替代了“独尊儒术”,以“胡汉一体”的“对外开放”取代了“故步自封”。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诗人李白、杜甫、王维就知道。他们一则诗仙(道),一则诗圣(儒),一则诗佛(释),缺一而不成其为盛唐。可见只有开放的胸襟,才有辉煌的文化。
然而,等到宋明理学来重振儒学时,帝国就不可救药了。本书无意评价宋明理学,也不认为它们就一无是处。事实上,问题并不在儒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,而在于再好的思想一旦独尊,都必然僵化。国家的统一不等于思想的一统。统一而不一统,则兴,盛唐是证明。统一而又一统,则亡,东汉是证明。如果冥顽不化地一定要坚持一统,那就最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激活生命力和创造力,魏晋南北朝是证明。
与思想禁锢相同步的是皇权的加强,始作俑者则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。西汉初年,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。国家元首是皇帝,政府首脑是宰相。皇帝所在曰宫,宰相所在曰府。皇宫相府,各司其职。皇帝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,有如董事长;宰相负责行政、军事、监察的具体事务,有如总经理。这原本是帝国时代最好的制度,却被汉武帝破坏。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,在皇宫之内另立“内朝”,以大将军统之,宰相(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)所在的相府则变成了“外朝”,等于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。此例一开,后患无穷。以后只要皇帝强势,就会破坏制度,侵夺相权。明的“内阁”,清的“军机”,不过是汉武帝“内朝”的翻版。然而汉武帝另设“内朝”,还只是一个公司任命了两个总经理。明清两代的做法,却是皇帝一个人既当董事长,又当总经理。帝国大厦独木难支,它能不江河日下吗?
实际上自盛唐以后,帝国制度就风光不再。之所以还能绵延不尽,除了我们民族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外,少数民族的不断输血也是一个原因。五代输一次,元输一次,清又输一次。每输一次血,民族精神就被激活一回。不敢想象,如果没有这些被称作“胡人”、“番邦”的少数民族,帝国的前途会是怎样?我想也只有两种结果。一种是像玛雅帝国那样彻底毁灭,另一种就是在死气沉沉中慢慢烂掉。不过,后一种可能性更大。
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也是糜烂。大清帝国的最后100年,仍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外交困。他们自己就是“胡人”,不能指望再有“胡人”来帮助。更何况,这一回来打咱们的,是英吉利人、法兰西人、德意志人、俄罗斯人和日本人。他们虽然比“夷狄”还要“夷狄”,却已经不再是“蛮族”,而是“列强”。这回,轮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西边去打猎(两宫西狩)了,和当年唐玄宗的仓皇出逃一模一样。
王朝气数,何以如此?
看来,我们还必须对帝国制度作进一步的分析,看看帝国是怎样一天天烂下去的。
文章来源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yizhongtian
关键词: 感悟转载
时间:2007年11 月25日,星期日,下午4:49。
通过 RSS 2.0 订阅源关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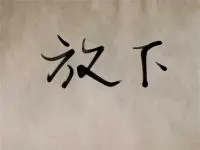
 lengven.com)
lengven.com)